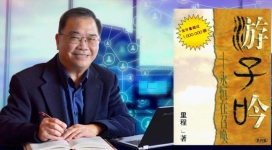文/扎克•易卜拉欣
在恐怖分子的家庭裡長大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扎克•易卜拉欣,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父親是一名埃及裔工程師,母親是一名美國教師。在易卜拉欣7歲時,他的父親開槍射殺了猶太捍衞聯盟的創辦者——梅厄•卡赫納。在監獄內,易卜拉欣的父親埃爾-塞伊德•諾塞爾參與策劃了震驚世界的世貿中心爆炸案。本•拉登曾因此號召世界要「銘記埃爾-塞伊德•諾塞爾」。
易卜拉欣的童年在四處搬遷中度過,為了躲避知道他父親的人而隱姓埋名。在恐怖主義陰影下長大的易卜拉欣,卻走上了一條和父親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他決定將自己的餘生致力於批判恐怖主義,傳播和平與非暴力。
仇恨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本能,而是一場精心編制的謊言。我的父親正是這一謊言的忠實信徒,而他曾一度想讓我也陷入這一謊言中。
1990年11月5日父親的所作所為,毀了我們一家。從此,我們的生活天翻地覆,充滿了來自他人的索命威脅和來自媒體的騷擾,流離失所,窮困潦倒,無數次想要「從頭再來」,卻每況愈下。父親的惡行史無前例,而我們則是被殃及的池魚。他是史上第一個在美國本土奪人性命的伊斯蘭教聖戰戰士,而支持他的正是後來自稱「基地組織」的海外恐怖組織。
然而鋃鐺入獄並非他恐怖分子生涯的終點。
1993年初,在阿提卡監獄服刑的父親與他在澤西城清真寺的前同夥一起策劃了第一場世貿中心爆炸案。這其中包括常戴氈帽和雷朋膠框墨鏡,被媒體戲稱為「盲人領袖」的奧馬爾•阿布德爾•拉赫曼。當年2月26日,一名名叫拉姆齊•尤塞夫的科威特籍男子和一名名叫伊雅德•艾莫爾的約旦籍男子執行了他們的計劃,駕駛著一輛滿載爆炸物的黃色萊德貨車進入了世貿中心底部的停車場。他們與父親有一個可怕的目標:讓世貿雙塔的一棟碰倒另外一棟,達到觸目驚心的死亡人數。然而他們最終沒有達到目的,爆炸只在樓底炸開一個約一百英尺寬,四層樓高的洞,造成約一千名無辜者受傷,六人死亡,其中一個女人懷有七個月的身孕。
母親竭力將父親的惡行瞞著孩子們,而當時年幼的我也一直盡力逃避這件事,因此很多年後,我才真正開始全面理解這場暗殺與爆炸的恐怖之處,而我又花了同樣長的時間,才開始真正直面我對父親對這個家的所作所為所感到的憤怒。在當時,我還無法承受所有的這一切。恐懼、憤怒與自厭在我的胃中翻滾,而我卻甚至無法開始消化它們。第一次世貿中心爆炸案發生後,我剛好十歲。但在情感上,我已經像一台關機的電腦。到我十二歲時,由於不堪忍受同學的欺凌,我甚至起了輕生的念頭。直到我快二十五歲遇到一個叫莎倫的女人後,我才感覺到自己和自己故事的價值。故事裡,被教導去仇恨他人的男孩,在成長為男人後,選擇了不一樣的人生道路。
我窮盡一生,想要明白是什麼讓父親走向恐怖主義的道路,而他的血在我血管中流淌這一事實,則讓我倍感掙扎。我想通過講述我的故事,帶給人希望與啟發,告訴大家一個在狂熱的火焰中成長的年輕人,如何走向一條非暴力的路。我不能對自己的為人誇誇其談,但我相信我們的人生都有一些特定的主題,而迄今為止我人生的主題就是:每個人都有選擇的餘地。就算你從小到大被教導要去仇恨別人,你也仍然可以選擇寬容待人,選擇將心比心。
父親因犯下滔天大罪而成為階下囚,使得七歲的我生活從此面目全非,但這也讓我的生活有了其他的可能性。在監獄中的父親,再也無法將仇恨灌輸進我的腦袋。更重要的是,他無法阻止我與那些被曾他妖魔化的人接觸,並透過謊言,發現他們也是人——我會關心他們,他們也會關心我。真實的經歷終將戰勝偏見。我的全身都在抗拒偏見的影響。
儘管家庭破碎,母親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始終沒有動搖,但和大多數穆斯林一樣,她並非一個宗教狂熱分子。當十八歲的我終於開始認識到一絲真實世界的模樣,我告訴母親我再也不在意每個人是什麼身份——無論他們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從今以後,我只在意他們是怎麼樣的人。她聽著,點點頭,説出了我這輩子所聽到過最有力量的幾個字:「我真的受夠了仇恨的滋味。」
她的厭倦並非空穴來風。這一路走來,她比我們都要更辛苦。有段時間,她不僅帶著頭巾,還帶著面紗,全身除了眼睛都包的嚴嚴實實:不僅因為她對信仰的虔誠,也因為她不想被別人認出來。
最近,我問母親,當1990年11月6日她和易卜拉欣叔叔離開貝爾維尤時,她是否知道等待我們一家的是什麼。「不,」她毫不猶豫地説,「我並不知道我將不再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不知道從此我的生活將一片狼藉,暴露在公眾視野中,不知道我們將被迫躲著媒體,和政府部門打交道,和聯邦調查局打交道,和警察打交道,和律師打交道,和穆斯林中的激進分子打交道。我像是跨過了一個人生的分水嶺,從此回不到從前的生活。對於前方的困難,我一無所知。」
父親被判處無期加十五年徒刑,無權假釋,現在在伊利諾伊斯州的馬裡奧聯邦監獄服刑。他的罪名包括陰謀叛亂、敲詐勒索殺人、對一名郵務員殺人未遂,受託開槍意圖殺人,以及非法持槍。老實説,我內心仍舊對他有一絲情感,一種難以抹去的情感,一種遺憾與內疚交織的情感,盡管它細如蛛絲。很難想像,當初我親愛的爸爸現在已經成為了階下囚,而我們都出於恐懼和羞恥改名換姓。
這就是為什麼二十年來,我從未探過父親的監。
(選自《我父親是恐怖分子: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作者是1993年世貿爆炸案策劃人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