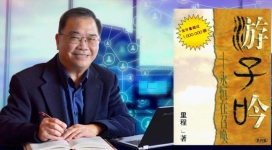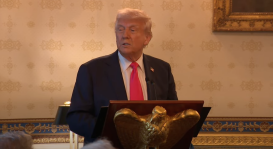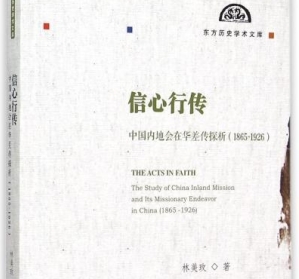
今年8月1日,《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此書經評審,入選《東方歷史學術文庫》。
執教於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胡衞清教授分析介紹中國內地會高度重視教會的本土化,要求傳教士穿華服,習華語,過平民生活,它對祭祖祀孔的不妥協與其獨特的神學立場和對《聖經》的理解有關,並非是保守頑固。從現代宣教學的角度看,中國內地會的神學觀念其實是相當先進的。它倡導信心宣教,重視巡迴佈道,強調人的屬靈需要,注重禱告,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建設本色化教會,重視本土教會的自治自養。
胡教授同時也評論本書對中國內地會這一「信心差會「的深度分析,對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典範意義。
以下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衞清教授之推薦序:
「2014年10月中旬,我赴台灣中壢市中央大學參加一場學術會議,會上台灣東華大學的林美玫教授告知她的大作《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經評審,入選《東方歷史學術文庫》,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簡體字修訂本。這是很高的學術榮譽,真的為她高興!林教授囑本人為她的大著作序。我與林教授很早就相識於學術會議,蒙其提攜幫助,與其請益交流,獲益良多,所以受命時雖覺惶恐,擔心難以勝任,但多年的交往,個人對林教授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所達到的學術高度,一直欽佩有加,常懷身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感。且林教授該著納入《東方歷史學術文庫》也是兩岸學術交流的一件盛事,值得慶賀,於是欣然從命。
林美玫教授在中國基督教史領域卓有建樹,已有多部學術著作面世,在海內外享有很好的學術聲譽與影響。《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是林教授研究中國內地會的專著,具有很好的學術品質,值得特別推薦。 首先,本書是兩岸三地第一本全面研究中國內地會的學術著作。既往漢語學界關於中國內地會曾有少量著述面世,或為傳教士個人經歷和生平事跡之英文著述的中文譯本,或以戴德生為中心探討中國內地會,雖各有其意義所在,但視界則有明顯的限度。林教授此書則從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播的大背景出發,詳述中國內地會的緣起與發展,分時段、分地區逐個考察中國內地會的宣教進程,總結其成敗得失。本書在這方面有兩個突出的貢獻:一是細致爬梳中英文史料,系統地進行整理,以省為單位製表,詳細列出傳教站、教士、本地教牧、守聖餐人數、受洗人數、學校、醫院等教務和事工方面的統計數據,這對於認識中國內地會在各地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二是書後的附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尤其是關於中國內地會的4個附錄最為重要。作者對於中國內地會中國助手的羅馬字拼音譯名、傳教士姓名的中英文對照、各地佈道所開辦時間以及中國內地會歷年經費收入都一一列出。從事教會史研究的人都清楚從英文資料中還原本土教牧的中文姓名以及查找傳教士中文姓名的艱難,而中國內地會是近代所有在華差會中傳教工場最為廣闊的差會,整理這些資料自然更加困難,真可謂字字心血,甘苦自知,我們從中也可窺見林教授的用功之勤、用力之深。
其次,本書對中國內地會這一「信心差會「的深度分析,對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典範意義。在近代,由英國傳教士威廉·克裡開創的「協會模式「(society mode)在大公會系統的傳教實踐中被廣泛採用,這種宗派差會像組建公司一樣,首先組建海外宣道會總部,由總部招聘各種類型的志願傳教士,派往宣教區,然後組建類似總公司分支機構的各宣教區教士會,經過多年宣教實踐後再組建類似子公司的當地教會。從一方面看,這種宗派差會似乎很成功,它們主動調適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系,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論是在沿海通商口岸還是在內地鄉村集鎮,它們將現代文明的要素輸入進來,它們開辦的醫院、學校以及其他相關事業都是當地進步的標志。而戴德生所開創的「信心差會「模式似乎是一個鮮明的反例,它堅持純福音宣教的方針,沒有創辦自己的大學,也很少開辦中學,醫院和診所的規模和水準都遠遜於上述宗派差會。在神學立場上,中國內地會對於中國社會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的祭祖祀孔,表現得比較強硬,不願做出妥協讓步。
曾有學者將李提摩太與戴德生做比較,對前者頗多肯定,同時認為戴德生思想保守。實際上,中國內地會高度重視教會的本土化,要求傳教士穿華服,習華語,過平民生活,它對祭祖祀孔的不妥協與其獨特的神學立場和對《聖經》的理解有關,並非是保守頑固。從現代宣教學的角度看,中國內地會的神學觀念其實是相當先進的。它倡導信心宣教,重視巡迴佈道,強調人的屬靈需要,注重禱告,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建設本色化教會,重視本土教會的自治自養,這與宗派差會的宣教戰略,形成了鮮明對照。宗派差會以西方母會為模板,要求本土教會亦步亦趨地去模仿,進而實現「三自「目標。宗派差會這種追趕型的「三自「戰略與中國內地會從一開始就實行本土化的宣教戰略孰優孰劣,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林教授此書為讀者認識「信心差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再次,本書作為中國教會史的專著,作者真正是在用「心「寫歷史。作者在分析問題時嚴守學術中立立場,力求客觀冷靜。不過,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林教授此書除了具備專門著作所應有的學術深度和高度外,還具有普通學術著作所不具備的「温度「,這種「温度「從展開書卷開始,如春風拂面,徐徐而來,温潤馨香,自有一種打動人的力量。本人數年前提出「教會史是不能用筆寫的,而是要用'心'寫的「,即是針對個人著述和一般教會史著作太過冷冰冰,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無法打動讀者有感而發。盡管看到了問題所在,但要解決起來卻十分困難,真正做到用「心「寫歷史、寫教會史談何容易。
其實,所有的歷史都是人的歷史,在教會史領域如果將個體的基督徒符號化,將他們的生命歷程和信仰抽像化,自然就會喪失教會史應有的底藴。理性分析與生命關懷其實不僅不矛盾,而且理應成為人文研究的必備要素。 社會發展需要目標,學術發展同樣需要目標。套用時語,中國需要夢,兩岸三地的每一個中國人都需要夢,只是這夢想需要有對生命個體的真切關懷才能打動人,需要有清晰的目標和堅實支撐才真正有力量。對中國教會史而言,它需要每一個參與者不僅投注其精力,更要灌注其生命,這樣我們的書才不僅有高度,更會有「温度「。筆者願以此與林教授共勉。是為序。
胡衞清 2014年12月 山東濟南」